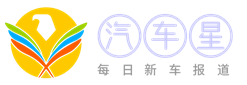清末民初,中国人已经在西医东渐的影响下,逐渐认可了女医存在的必要性。《富马利中国见闻录》记录了中国第一所女医院校——广东女医学堂及附属柔济医院(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创办者富马利在中国行医期间的见闻。
本文摘自《富马利中国见闻录》([美] 富马利 著 / [美] 露西·皮博迪 整理,杨智文、陈安薇、黄勇译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版)译者序,注释从略。标题为编者所加。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富马利中国见闻录》书封
Mary H. Fulton,中文译名富马利。1854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阿什兰。根据原书摘录的来自《阿什兰公报》的报道,她的父亲富尔顿将军是“阿什兰最伟大的法学家和俄亥俄州北部最著名的法律代理人”,母亲富尔顿太太曾是阿什兰“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兄长富尔敦为美国长老会牧师,1880年就来到中国传教。而富马利本人曾就读于威斯康星州阿普尔顿的劳伦斯大学,1874年毕业于密歇根州希尔斯代尔学院,1877年获硕士学位,随后任教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学校,1880年进入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学习,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富马利于1884年受美国长老会派遣,以医学传教士的身份前来中国。自此之后,除了中途曾经两度回国休假外,一直留在中国,至1917年方退休离开。在中国逗留的三十多年间,富马利主要从事了行医、传教、翻译外国医学著作等工作。她对中国近代医疗影响深远,不仅把为数可观的中国女性培养成为专业医护人员,为大量中国妇女儿童提供了医疗服务,还一手创办了柔济妇孺医院、夏葛女医学堂与端拿女子护士学校。其中夏葛女医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女子医学校。

富马利医生肖像图
……
要了解富马利创办三所医学机构的意义,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女医群体的发展历程。近代以前的中国,由于性别之间的隔离,男性医者要涉及女性医疗难度很大。北宋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提及:“治妇人虽有别科,然亦有不能尽圣人之法者。今豪足之家,居奥室之中,处帷幔之内,复以帛蒙手臂,既不能行望色之神,又不能殚切脉之巧,四者有二阕焉。黄帝有言曰: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色泽以浮,谓之易已;形气相失,谓之难治;色夭不泽,谓之难已。又曰:诊病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若患人脉病不相应,既不得见其形,医人止据脉供药,其可得乎?如此言之,乌能尽其术也。”按照寇宗奭的说法,男性医者难以为女性患者提供治疗,主要是因为无法充分运用望闻问切四诊之法。南宋陈自明在《妇人良方》序言中也提及:“世之医者,于妇人一科,有《专治妇人方》、有《产宝方》。治以‘专’言,何专攻也;方以‘宝’言,爱重之也。盖医之术难,医妇尤难,医产中数体则又险而难。”明代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也提及女性疾病之难治:“谚云:宁治十男子,莫治一妇人。此谓妇人之病不易治也。何也?不知妇人之病本与男子同,而妇人之情,则与男子异。盖以妇人幽居多郁,常无所伸,阴性偏拗,每不可解,加之慈恋爱憎,嫉妒忧恚,罔知义命,每多怨尤,或有怀不能畅遂,或有病不可告人,或信师巫,或畏药饵,故染着坚牢,根深蒂固,而治之有不易耳,此其情之使然也。”通过这些论述可知,近代以前的男性医者对女性病患充满偏见,将为女性提供医疗视为难事。
男性医者在女性疾病治疗方面的无能为力,为女性医者的介入提供了空间。有学者认为,明代以前的女医以道教医者的形象出现,“似乎也享有社会地位与游走活动的充分空间”。南宋时期袁采在《袁氏世范》中告诫道,“妇人以买卖、针灸为名者,皆不可令入人家”。由此可知,当时女性医疗者从事的领域包括针灸。这些女性医疗者的出现对于女性患者而言自具有正面积极的影响,然而在男性士大夫眼中,她们却成了需要防范的对象。元代以后,女性医者被纳入“三姑六婆”的范畴,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就提及:“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也。盖与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奸盗者,几希矣。若能谨而远之,如避蛇蝎,庶乎净宅之法。”“六婆”中的药婆、稳婆正是当时的女性医疗从业者。只是在陶宗仪等士人眼中,这些女性医者是需要“谨而远之”“如避蛇蝎”的。
至明清时期,有关女医的记录明显增加,显示女医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有研究指出,明清时期新安地区(包括今安徽黄山、江西婺源等)已经形成了女医群体,她们类型多样,医术来源多元,在明清徽州社会医疗中有着广阔的生存空间,与男性医家一起构建了徽州民间医疗的大环境。一些儒学世家也会有意识地培养家族中的女子学习医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明代无锡的谈允贤。根据她在《女医杂言》一书中的自序,谈氏一家“世以儒名于锡”,曾祖父“赠文林郎、南京湖广监察御史”,祖父“封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兼以医鸣”,父亲为“莱州郡守,进阶亚中大夫”。谈允贤本人年幼之时,即已在祖母的教导下阅读《难经》《脉诀》等医书,至出嫁后,子女如果患病,“不以他医用药”,而是在祖母指导下亲自用药。祖母离世前将“素所经验方书并治药之具”尽数传授给谈允贤,使谈允贤医术精进,终成名垂青史的女医。
尽管女医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但在掌握书写权力的士人群体眼中,女医依然是一个被诟病的社会群体。在士人眼中,女医被诟病主要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专业医疗知识的匮乏。万四妹在考察明清新安女医的情况时就指出:“新安女医活跃在民间,凭借性别优势进入闺阁,为一般女性患者提供日常医疗服务。她们在民间行医的事迹,往往不见于正史,而是在一些新安男性医家医案中被作为误治的反面例子记载下来。……这些记载,一方面反映出新安民间确实存在着一个女医群体;另一方面又反映出,这些女医由于没有受过良好的医学教育,医疗水平不高,使用的皆是‘草头方’。”梁其姿分析指出,像谈允贤这种“有素养的、遵循正统医道的女医,则产生在理学发展的晚期,主要在士族中。然而,这些少数女儒医的影响力却受限于家族之内”。二是“三姑六婆”始终是女医群体没法摆脱的标签。明清以后,人们对“三姑六婆”的形象形成了刻板的认识,其中包括“唯利是图”、“败坏封建道德”、“不守本分”、“软弱怕事”等。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讲述了一个“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身为富商女儿的周胜仙之能与在樊楼卖酒的范二郎私订终身,主要因为王婆的撮合。而书中的王婆正是一个典型的“三姑六婆”形象:“他唤作王百会,与人收生,作针线,作媒人,又会与人看脉,知人病轻重。邻里家有些些事都浼他。”
直到近代以后,中国女医的社会地位才开始上升。梁其姿形容这种变化称:“到了帝国末期至近代,此种正统女医楷模的普及化终于迅速地实现了。”女医地位上升的契机之一,是西医东渐背景下外国女医在中国的活动。外国女医往往接受过正规的近代医疗教育,拥有较为专业的医疗技术,且因其性别优势,比男性西医医生更能满足特殊群体的医疗需求。1884年创刊于广州的《述报》在报道中提及:“近闻通州北后街美国传教馆设立多年,时有医者,由外洋来此施医,并不茗名,就医者甚属寥寥。兹有厚大夫系女医,侨寓通州二年有余,施医赠药,无不立效。城乡就医者颇多,尚有数十里外来者,足见其名播四海,恩及群黎也。”即便是达官贵人也需要求助于外国女医,比如李鸿章在1879年与1882年两度邀请美以美会派驻中国的女医生赫慧德(Leonora Howard)为自己的母亲、妻子治病。
外国女医的到来,让中国社会得以重新审视女医存在的必要性。1861年英国字林洋行创办的《上海新报》报道称:“夫世人生病,内外分科,男女有别。譬如女人生内症外症于下体,男医颇难看视。病女碍于羞耻,即上体亦多未便。再之外国生产皆归男医,接生虽经此例,似不成规矩。近来外国女医生专能治医各种内外症候,亦照男医例考校,得国家取其等第凭据,将来各分男归男医,女归女医,岂不至善也。而中国聪明能干妇女,或本是医家,或至戚行道,皆可学习医理,亦可悬壶专治女科,诸多便当。而中国收生,例有稳婆,小孩抹惊、推拿等症,亦见多有妇女为。兹外国还设女医,中国便可效尤也。但凡事择善而行,凡有所长,均可效法,断不可一偏之见,自恃己能为至矣。”这篇报道明显已经抛弃了传统士人对女医的歧视与偏见,提倡中国当大力培养女医。另一份在上海地区发行的《万国公报》于1877年刊登了《西女习医》一文,介绍了瑞士培养女医生的情况:“瑞士国,欧洲法、德、意三国中间之国也,境内有城名曰祖理戈城,中有大书院,素为男子励学之所。迩时亦准女子入院习夫医学,均非由招生而至,尽属诚慕自来,其女子率多俄人,于耶稣后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时,有俄国女子投首请学医于院中,院众允其请,容留之,此祖理戈城书院有女子习医之初。”
近代以来男女平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构成了中国女医地位上升的一个重要背景。清末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小说《精卫石》中,就借书中人物之口宣扬这样的主张:“大家都入学堂的,教育无非彼此间求得学艺堪自立,女儿执业亦同焉。有许多女子经商或教习,电局司机亦玉颜。铁道售票皆女子,报馆医院更多焉。银行及各样商家店,开设经营女尽专。哲学理化师范等,普通教习尽婵娟。人人独立精神足,不用依人作靠山。”在秋瑾看来,男女平等的前提首先是男女拥有平等的就业权利,而医生也是秋瑾认为的女性可以从事的职业。1916年,胡学愚在《东方杂志》上刊登《女医之今昔观》一文,其中提及:“识者多谓今日妇女业医之发达,实近世女权扩张之结果,熟于掌故者则不谓然。盖就实际言之,世界人种开化之先,无不以妇女司医药之任。其后男子权力发达,疗病之职始移诸男子之手中。十五世纪之初,欧洲诸国之男医生曾缔结同盟,排斥女子之业医。降至十九世纪,女医势力乃复膨涨,渐复古代之状况云。” 按照胡的说法,女医之兴衰实与男子、女子权力消长有莫大关联。《光华医药杂志》在1934年也刊文谈及女性习医对于促进女子自立与社会改良所具有的作用:“医学为科学之一,无论任何方面观之,皆切要不可缓之一学科也。而况吾国,而况吾国之女子?吾国而不欲自立则已,欲自立也,必由女学始。吾以女子不学自立则已,欲求学以自立也,必由医学始。吾尤敢断言:女学不发达,则愚昧无救!女医不发达,则沉疴难挽!既愚且病,则又将何所籍以改良社会之用耶?故欲改良社会,必女子人人有普通医学之知识。”
富马利初抵中国之时,中国人已经在西医东渐的影响下,逐渐认可了女医存在的必要性。富马利已经感知到中国妇女对于女医的需求。她在原书中提及:“对于中国女性而言,女医生是无可替代的,因为她们拒绝男医生的治疗。”然而,就她所见,当时广东称得上及格的女医可谓寥寥无几,除了同为美国医学传教士的赖马西之外,富马利接触到的女医就只有曾经跟随嘉约翰学医的中国助手梅阿贵。随着她在中国逗留时间的延长,她对清末中国女性的痛苦遭遇有着更为清晰的认知。由于迷信,病人家属往往无法配合富马利的治疗,导致病人难以痊愈。有一次富马利在对一名女病人进行施治时,要求病人家属提供帮助,但病人家属认为提供帮助会给其他家人带来不幸而予以拒绝。又有一次,富马利正在为一名年轻母亲进行治疗,其家人却跑进来把一口锅猛砸到地上,说是这样做有利于驱逐邪灵。另外,富马利还多次遭遇这样的情况:女性患上了大家认为的绝症,家人们提前给她穿好寿衣,将她安置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任由她自生自灭而拒绝施救。
更为可怕的是,当时中国女性的命运往往受其父亲、丈夫或婆家的左右而无法自主。富马利的见闻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国女性的实际处境提供了大量材料。根据书中记录,富马利曾经前往一个家庭提供诊疗服务,这个家庭的母亲非常自豪地向富马利介绍她的13名儿媳。富马利开始时还以为这名母亲生了13个儿子,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名母亲只生了3个儿子,而其中1个儿子就拥有了7名妻妾。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富马利感叹道:“每个男人的妻妾都成了婆婆的奴隶。”早期担任富马利医疗助手的梅阿贵,8岁时就被父亲卖掉用以抵偿赌债,后来又数度被卖,嫁的丈夫也是买家中的一员。丈夫死后梅阿贵跟随嘉约翰医生,最终成为一名妇科医生。但即便如此,她依然未能摆脱亡夫家人的束缚,亡夫的叔叔还想把梅阿贵卖掉换钱,她最后还是依靠嘉约翰、富马利等人的帮忙才得以脱身。又如富马利的学生罗秀云,在14岁时被家人以125美元的价格卖给一名男子为妻。这名男子在婚后前往纽约,而罗秀云则留在广州,进入富马利开设的医学堂学医,最终成为一名医生。但就在罗秀云事业有成之时,她的丈夫回来了,要罗秀云放弃一切跟随他前往美国。罗秀云不肯,她的丈夫就想强行把人带走。最后是在富马利的协调下,罗秀云承诺归还丈夫给她家人的钱财,而她的丈夫则给了她一纸休书。

柔济妇孺医院人物照片。从左到右:富马利、夏马大、罗秀云。
目睹了清末民初众多女性的悲惨遭遇后,富马利认为,女性地位之所以不如男性,是因为她们无法独立赚钱。如果她能够将更多的中国女性培养成医生或护士,那这些女性就能独立赚钱,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富马利的记载为我们揭示了富马利创办三所医学机构前的心路历程。她算了一笔账:一个普通的秀才,每个月通过教书能获得相当于8美元的收入;而一名护士每个月最少能有相当于15美元的收入。基于这一想法,富马利决定在广州创办妇孺医院和女医学堂。根据香港《华字日报》的报道,我们知道最迟在1897年,富马利即已萌生了为中国女子创办一所医院的想法。报道称:“百余年间,西医航海东来,以其海外奇方匡中医所不逮,存活救济之功颇为不小,前时之种洋痘,近时之接牛割症,皆著奇效者也。省城虽有医院,尚无专设女医院以便妇人,本馆经著为论说矣。兹闻美国富氏女医生久寓羊城,济人念切,龙宫探秘,三折其肱。现拟在省创建妇科医院一所,兼理儿科。盖西国无论男女,习内外科皆须由医院学成,考试数次,其术确可医人,方给以文凭,行世治病。非若华医之用指忖测,药性未谙,遽出而悬牌市上也。该富女医名动中西,术经屡验,前出使美国容纯甫副使解囊相助,并广劝签题督宪谭宫保、抚宪许中丞、将军保留守及司道各大宪,均乐为捐奖。诚以富氏善举,可嘉其医道,亦极精确。将来此院落成,儿、妇两科,必多人学习,慧心仁术,海外春回于吾粤,妇孺大有裨益。又闻该院择地拟濒临海滨,以便舟楫来往。经之营之,想不日成之矣。” 根据这篇报道,富马利在1897年时就已经选好了“濒临海滨”之地,作为日后建设医院与学校的地方。富马利在信中提及建医院前这块“濒临海滨”之地的状况:“我们找到了一片开阔的土地,有200头猪正躺在泥泞里,北边的河流上架设了一些矮小的棚屋。每天晚上棚屋里的猪被驱赶出来,养猪的人全家睡在猪圈的上层。西边有一个染坊,染坊后面是一个兵营,每天早晚传来大炮轰鸣的声音,东南角则堆满了周边汇集而来的垃圾,传来难闻的恶臭。”在当时,恐怕就连富马利本人也不会想到,这一片充斥着泥泞和恶臭的猪场,后来会被改造成环境优美的“拉法埃脱大院”,而柔济妇孺医院、夏葛女医学堂及端拿女子护士学校等三所医学机构皆在此大院之内。
《富马利中国见闻录》一书的翻译能帮助中国的读者从更为多元化的视角去看待富马利创办三所医学机构的历史意义。如今我们评价这三所医学机构创办的价值,都着眼于医学的层面。《富马利中国见闻录》一书则引领我们去思考三所机构创办的社会意义。对于当时很多中国女性而言,这三所医学机构的出现改变了她们本来悲惨的命运。比如说罗秀云正是因为在夏葛女医学堂学医有成,最终得以摆脱不幸的婚姻,在这个曾经歧视女医的国度获得“女医神技”的美誉。 又如原书提及,罗秀云曾经收养一名被遗弃的女童。这名女童遭遇遗弃完全是因为父母无力供养,又找不到买家把她卖掉。幸亏这名女童最后被带到了柔济妇孺医院,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书中还提及富马利的前保姆在夏葛女医学堂学医有成,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才避免了她妹妹因食物缺乏而被卖掉的命运。可以说,富马利创办的三所机构不但挽救了大量女性的生命,更让不少女性获得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
富马利创办的三所机构历经演变,在中国近代医疗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夏葛女医学堂的前身是富马利在1899年创办的广东女医学堂。至1902年,为了纪念夏葛先生对学校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更名为夏葛女医学堂。后来学校经历过多次改名,至1936年并归岭南大学。虽然仅仅存在了30多年,但培养了大批掌握先进医疗知识与技术的中国女医生。根据相关统计,直至1933年12月,全国列入统计的医学院校有28所,其中只有夏葛医学院与上海女子医学院招收女生;1932年全国医学毕业生3655名,女生有619名,其中就有214名是在夏葛医学院毕业的。 由此可知夏葛女医学堂在中国女医的培养方面发挥了何等作用。
从夏葛女医学堂毕业的女医生不但为近代中国女性医疗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也积极参与当时的各项社会活动。如1905年的毕业生梁焕真,在1907年加入同盟会,与徐宗汉、高剑父、胡毅生、朱述堂、朱执信等人组织广东革命办事处,以梁焕真的医务所作为秘密基地,暗地里宣传革命思想,发动了很多医学生入会。1916 年的毕业生伍智梅,为同盟会元老伍汉持之女,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1919年在广州参与组织广东女界联合会并当选为第一届理事,后与何香凝等人发起创办贫民生产医院,还参与了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创办。2017年5月27日至10月12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举办了“女界先锋——伍智梅生平史料展”,展现了伍智梅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如夏葛女医学堂第四届毕业生姚秀贞,为近代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表妹,于1908年在北京开设了“秀贞女医院”,是我国第一代私立女子医院之一。
夏葛女医学堂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影响力,曾引起孙中山先生的关注。《富马利中国见闻录》收录了宋蔼龄女士在1912年5月7日给富马利写的信(此信原件藏于广东省档案馆),里面提及孙中山先生要在5月15日前来参加夏葛女医学堂的毕业典礼。省档案馆里还藏有孙中山视察学校时留下的与夏葛女医学堂教师、学生的留影。

孙中山1912年视察柔济妇孺医院时留下的合影。
至于柔济妇孺医院,根据相关记录,富马利于创办广东女医学堂时,还附设了教学实习医院,1902年医院建筑落成,更名“柔济妇孺医院”。至1930年由美国长老会移交中国政府,从此开始了华人自办的新阶段。1954年由广州市人民政府接管,改名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2006年转为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2013年6月因广州医学院更名为广州医科大学而再度更名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从1902年至今,历经百余年,该院为广州地区的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端拿女子护士学校则是富马利在柔济妇孺医院开业后为解决护士来源问题而开设的,至1951年改名为广州私立柔济医院附属护士学校,1953年更名为广州市第二护士学校,1958年改名为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护士学校,1975年改名为广州市第二卫生中等专业学校并脱离医院独立建制,至1980年更名为广州市护士学校。1998年5月,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广州市护士学校与创办于1935年的原广州市卫生学校合并为广州卫生学校。 2005年3月,广州医学院在整合原有广州医学院护理系、广州卫生学校、广州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资源的基础上,成立了广州医学院护理学院。
《富马利中国见闻录》里提及富马利在三所医疗机构创办后的欣喜之情:“我们的‘猪村’终于开花结果了。”如今这“果实”虽然历经百年,但依然散发着迷人的芳香。